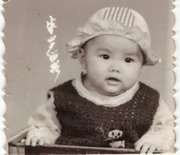除夕前夜
远远近近都是花炮的轰响,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在辽阔的夜空回荡,年已经开始了。描绘这个时刻最精彩的文字对我来说就是《祝福》结尾的那几句话,从小到大在家过的二十多个春节,印象最集中的就是旺盛的香火给神灵享用,喜庆的硝烟中众神蹒跚,大红的灯笼、大红的对联、花花绿绿的门旗昭示着对春天的期待……只是从来都没有准确的记住或者背下从学到那篇课文之后,就深受感染的那几句话。
小时候的联想能力已经在逐渐丧失,现在看到文字大多时候也只是文字而已,甚至看到鲜亮个性的形象还只是那个形象,已经不会有联想,当然,说到原因,除了上面说的联想能力,有时候,我会不甘心的想,大约我看到的那些东西本身就不鲜亮,或者说只有个鲜亮的外表而已,文字也只是文字而已,没有什么值得人去联想的意象,所以,人们也就拒绝联想,拒绝哪些东西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电视频道转到中央十一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黄土地原生态艺术绝响晚会的东西,一帮七十多岁的关中庄稼汉在巨大的舞台上唱“灯影戏”(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皮影戏或者影戏),我很诧异,这个东西怎么就变成了绝响?!童年的时候,灯影戏就是暑假的标记。我们那里管夏忙之后、秋种之前的那段时间叫“忙毕”,有几分古文意思,但是望文生义也知道就是忙碌告一段落完了,可以休息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是三伏的时间,天气热,地里也没什么事情好忙,所以四乡八村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地赶庙会,庙会当然需要有个热闹来吸引人流,另一方面也要有个献给各个地方敬供的不同神仙的礼物,所以,每个暑假就会有几乎看不完的灯影戏,当然,也会有所谓的大戏,就是县里或者市里剧团演出的戏,这个戏有大舞台,有灯光,真人演出,年景好,人们心气也高,又有德高望众的组织者的时候,这种大戏回偶尔替代灯影戏,这时候,庙会自然就变成了乡间大事,但是,一般情况下,灯影戏还是庙会地主角:晚上八九点,喇叭啸叫过之后,人们就纷纷前往麦场里那张电影幕一样的东西前面,远远看去,就像夜空打开的一扇窗户,习习凉风中人们就在自家门前开始享受惬意的一晚。白天下午,唱不了灯影,就几个人围在一起,在树荫下敲打起来,这叫乱弹。
之所以说灯影戏是我们这些小孩子暑假的标记,是因为庙会唱灯影戏的时候,各种小商小贩就会从各处聚集到会场,兜售各种东西,我们就可以在“琳琅满目”的摊点之间乱窜。那是我们孩子地节日,不单能从大人那里获得几张毛票,自己作出消费一下,给自己买本小人书或者塑料宝剑,还能美美地解馋,一连几天都吃上家里招待亲戚地臊子面,妈妈做的臊子一整年里都是我们企盼地美味,除了春节,一般就只有赶会地时候能吃到了。
如今,那些灯影戏竟然已经变成了绝唱!“三分钟年华老去”,不知道是谁一语道破天机,大约我们那样的童年也早就成了绝唱,而不去细想却很难自知。
从九八年忙毕离开家乡到现在,说起来只是很少的几个数字:四年,那是大学本科的学制时间;接下来三年,然后又是两年;减法得出的数字是九年;回家的次数没有统计,大约就是十几次;按照既定的套路,人们会说我大学毕业长大成人了……我们只是在长大,我们在迈向充满光明的新生活&未来。我几乎从没意识到八年十年对曾经我熟悉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对爸爸妈妈他们意味着什么。
“三分钟年华老去”,十年八年亦是弹指间啊。
有一个春节来临了,用电影里的话说,就是“2006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第一次没在家过年,却又在家为春节做着准备。一个颇有意味和意义的春节:2006年,用小羊的话说,我们完成了人生大事。我们组建了我们的新家庭,我们分别多了一对父母,多了一份关爱和挂念。想到这点,我就不再感慨年华老去,而是看到闪光的年华。
千言万语汇集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句话都说不出。一篇散乱的记述在荡漾的花炮声中写下,“怀念我们共同走过的2006”。
用《祝福》描写的年节的那段我没背下的那段话作为结尾,祝福新年,祝福圆溜溜的猪年: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