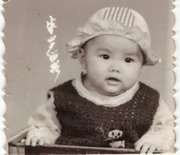刘震云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论述听上去很辩证,大致的意思是悲剧的核是喜剧,而喜剧在往上才是真正的悲剧。就像人的生死两头很显然是悲剧,哭着来到世上,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去往“一劳永逸的长眠”(这个是余华的话),而中间部分则是以各种各样的喜剧进行的。
《长江7号》似乎在印证这位作家的论断。
如果作为儿童片,《长江7号》绝对是纯粹意义上好看好玩的儿童片,小孩子的幼稚与狂妄想法、以及小孩子之间那些“残忍的好奇心”促成的种种事件,被夸张而准确的展现出来,加上那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独创的、天真可爱外加周星驰式调皮外星机器狗“7仔”,绝对能让小孩子度过一段开心时光,然后在内心里种下向善的种子。至于大人,如果不被所谓专业眼光毒害的太深,或者还不至于早衰式的死气沉沉肌肉僵硬,估计也会忍不住会心一笑,在瞬间远离眼下这在如浮沉般翻滚的新闻中变得更加寒冷冰冻而且有些沮丧的冬天。
但是,周星驰这次演的是个民工。用片中儿子的话说,爸爸的职业是:做民工。这位父亲邋遢黑瘦,要在他做建造的水泥大楼顶上吃盒饭,蹲在商店橱窗外看电视,想尽办法来疼爱并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己无法拥有尊严或者得到尊重,那就要让孩子与自己不同。
尽管他对用“柔软的方式来面对坚硬的现实”这种方法早就稔熟于心,故事也试图用外形机器狗狗的神力来遮盖或者置换他注定的命运,但情感的转移以及他的死而复生却更加让人感觉世事炎凉,蜻蜓点水般触摸到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
我们在看大陆电影(现在似乎港片以及合拍片都统称国产片了)的时候,或者看港片偶尔联想对照到大陆片的时候,会轻易就顿悟:哦,我们所谓影星在电影里塑造的是自己,而人家所谓的艺人往往能成为角色。自从有一天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吃惊竟然有初中生批判大陆电影以及所谓的电视电影:“我坚持我下看,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还能假到什么地步”。
很多因素决定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标准,就像单位里你会是局长、老张、小李,而在社会上你变成干部、城里人、乡下人,城里人又分成白领啊、干部啊、工人啊什么的,乡下人里当然也有干部,但对乡下人的准确称为应该是农民和民工,前者说明他的户口所在地、真实职业以及所谓文明程度,后者旨在揭示其在高度文明的现代大城市里的地位,首先要表明是个外来者不是主人但也绝对不是客人,然后是低标准生活的主体,不懂规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应该必需承担挖地沟、捡破烂、倒垃圾、修管道等等所有苦力范畴内的活儿,而且应该感恩戴德。
然后,所有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等都自然而然淹没在这些身份概念之中,如果直白的说,就是身上戳有肉牛、种牛或者耕牛之列标签的畜生?!!!
既然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既然我们是坚决的唯物主义者,既然我们信奉物质决定意识,既然物质也就是客观存在(记不清楚了),那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意识与物质的相互纠缠,有意为之的张扬和深藏不露的隐匿之中,生活的正剧无可逆转的就变成了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