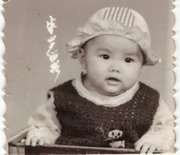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一对农民夫妇史诗般的流浪生活。”——小说作者给小说的副标题。
史诗不史诗的,我想不仅农民不懂,即使是城里人绝大多数也不会很了。
不过你看,一张口,我们就很自然地把这两群人区分开讨论:农民或者农村人,市民或者城里人。老马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你本身就是制度的产物,所以你的意识基本上也就是这个物质的产物,发育正常。
拿到《盲流》这个小说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当初看了前言,自己觉得基本上可以揣测到故事的内容,觉得调子可能会偏“灰”(这是这两年学会的词汇),所以就没仔细看。这两周,电视上热播一部关于“城乡结合婚姻”问题的电视剧,看到电视台推出的话题讨论互动平台上人声鼎沸,感觉很关心此类问题的,于是,就把小说拿出来看。
小说不是很长,故事也不复杂,讲的是淮河边上一个有长期“要饭传统”孙佃铺村一对农民夫妇的故事,主人公叫孙国民。此人因为算的上是村里的文化人、又有一手吹唢呐的好手艺、为人也宽厚,所以,在村里过得是“上层建筑”的生活,老婆苏桂芬就是因为这个嫁给他、也是因为这个崇拜他、愿意事事都跟随他。但是,孙国民不如意的地方,也是让他在村里人,尤其是无赖孙建兵面前抬不起头的地方——结婚几年,还没结出一星半点的果子。
为此,孙国民开始了一个“大计划”(借用一下尚敬不温不火的新作《房前屋后》里面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有个孩子,还要不止一个孩子。
这是尊严问题,男人的尊严问题。
孙国民让苏桂芬伪装孕妇,然后设法去买孩子,先是遭遇骗子,后是人贩子被抓,孙国民的一点积蓄基本上都打了水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医院等候上天怜悯的时候,果然,有人把一个女婴放在了他身边,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孙和栩。
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实际上应该是逃避自导自演的故事不漏出破绽),也是为了这个孩子(被诊断发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孙国民夫妇卖掉了祖宅,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
谋生是艰难的,即使是捡破烂这个行业,不但各地都被各种势力范围占据,而且竞争还十分激烈,更要命的是,他是个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到任何城市,都有可能称为被治安清理的对象,人们很自然的就把他们当成要饭的(尽管孙国民从来都严守他自己关于要饭和讨生活的界限)和盲流。即使是这样,他还是用十几年的时间,在一遍又一遍被遣送之后,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城市(孙国民最后自己总结,那是不花钱旅游)。
其间,他遇到过不少好人,当然也有坏蛋。他的孩子从一个变成了五个,但是没有一个是他亲生的:孙和柱是他收养的流浪儿,孙和美、孙和丽是被杀害的陈老板夫妇的遗孤,最小的是在大街边的草丛里捡来的。他们不仅抚养了这些孩子,还教会了这些孩子吹唢呐,做好人。
但这是一段没有尊严的漫长岁月。
孙国民却始终坚持天上会出太阳,地上会长粮食,没有一天耽搁的,那是老天爷叫人好好活哩,而他像草一样活着的目标,就是这些孩子,这些即将不再是黑户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当他们怀揣着用吹唢呐赚来、从牙缝里、衣服上扣掐出来的巨款终于回到孙佃铺的时候,这个目标就不远了。
故事一点也不伟大,只有那么一点点现实。 盲流,这就是一对盲流史诗般的流浪生活。
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说,孤立和打败恐怖分子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也是观念之间的斗争。这个说法很高明,农民的背面就是盲流,法律没有规定,制度也没有这么赋予,但历朝历代历人观念上都是这样,连斗争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