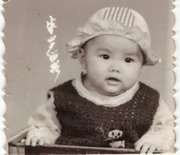习惯标准语言的人似乎不怎么用这个词,为找到这个词我竟然费了好半天劲儿,证明我也不知不觉皈依了标准派,这个历程近乎十年。但是,似乎我六根未净,并未真正皈依,对家乡的表达方式略显生疏之后,却并未对标准语言有所精进,结果现在不论是论起“道”来还是说起“书”来,连自己都感觉索然。
既然找到了响动这个词,还是返回来继续说响动。
老家的房子一般都有阁楼,所谓阁楼并不是西洋电影里那种可以居住的小半层屋子,只是为了让屋子的空间更紧凑,不至于躺在炕上,坐在椅子上就看见屋顶上的梁椽,在屋檐的高度顺着椠架上死条木梁,篷起一个平整的天花板而已。这个天花板因人而异,有实力的人家,用的平整的木板,整齐密实,就像现在城里人铺地板那样,弄一个天花板,这样的天花板上放的空间可以成为真正的阁楼,其高度虽不可以居住,但其牢靠程度却足以把成石的粮食存在上面。没实力的人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一而足,当然最简单的是什么都不做,除此而外,一般会用芦席加细竹棍儿篷上,下面再糊上报纸、小孩的正反面写过的作业本之类的。
详尽的解释老家的阁楼,通常犯这样的毛病恐怕是潜意识作祟,那个不只是本我还是自我还是什么我的家伙在谴责我不要忘记,而我却常常不会想这些陈芝麻,所以忘本的内疚或者健忘的惶惑让我染上了絮叨的毛病,今天倒不是这样的情形,显然阁楼的事情是我主动想起来、说起来的,解说它的原理,是因为最初对于响动这个词的生动理解是从它而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随着爷爷奶奶睡,那一段时间“响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爷爷奶奶的瞌睡已经不像我那么多了,所以,对于阁楼上老鼠的响动,他们总是很敏感。有一段,老鼠特别猖獗的时候,奶奶会在枕边准备一支细长的竹棍,用它来对付半夜出动的老鼠。当老鼠在黑暗中快速跑动时,奶奶的芦席顶棚便会火车驶过一样,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这个时候,奶奶就会挥动竹棍,胡乱敲打几下,制造些声响,让那轰隆声止歇一会儿。
我猜想那些半夜来我家顶棚上的老鼠,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要是放在解放前,我们家的木头阁楼上或许会有成囤的粮食,那个时候要粮的角色多,跑开穿各色制服的,还有土匪什么的,粮食放在阁楼上或许还有希望逃过一劫,那年头像我们家这样需要亲自挑着筐拾粪、自己下地干活、吃花面馍的小地主,估计是真正的“地主家也没余粮”。但有的话,应该肯定在阁楼上。
所以,从旧时代,估计老鼠们就口口相传,形成了阁楼上有粮食的共识,及时是时代变了,我家的木板阁楼变成芦席顶棚,木板阁楼时代那些老鼠的后代们还都执着于他们的传统,用他们轰隆隆火车般的跑动,搅扰奶奶的水面,要奶奶听见他们的动静,就要制造代表主人存在的响动。
那个时候,我形象的记住了奶奶说的响动这个词,其实应该是动响,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
关于响动的第二层含义,与响器这个词有关,响器无处不在,但在寺庙、锣鼓队、乃至吹鼓手、剧团里到处都是。村里唱大戏,有经验的大人们,总是在舞台那边传来吹打声的时候,才背起手,慢悠悠的出发,性子急的人就会说,台子上已经响动开了,得赶紧些。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终年宁静的村子上空忽然飘动的响动,常常会让我们激动地不知所措,既想在戏台周围乱窜,不错过任何热闹和大家的目光,又向不错过院子来之不易的响动,那响动远远的传来,有些空空旷旷,却充盈于每个人心里,告知大家我们处在不同以往、易于平日的时间和事件中。
我始终没有学会向作家描写夕阳像闯祸的篮球跌进窗花那样,描绘让自己激动乃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在某些时候,摆脱不了那种情境:既是热闹人群中的一员,又能抽身出来看到包括自己的热闹人群,就像自己想看到自己开着的车子在路上怎样行使那样。
从小年夜开始的爆竹声今晚依旧,城市的夜空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变得活泛了一些,我知道那些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散播到空气中除了火药的香味,还有放鞭炮的人难得的一个人面向位置数目的大众无拘无束的表演和宣告。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除夕夜仔细回味连绵不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我知道那响动中有众神在蹒跚中享用烟火,还有就是远远近近、各不相同的人在夜空中相互传达着相似的信息,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满满的,因为我知道我的鞭炮声别人也已经听到了。于是,这响动又会我的激动乃至不知所措,在除夕的夜晚不想睡觉,有无所事事,于是,我就回想:鞭炮大概是放给远方乃至过去的人听的,我要是能在远处听自己放的鞭炮就好了,就像除夕之夜,偷偷出来看窗花彩联的窗前漏出的喜庆那样。明天要回家团聚了,今晚在家洒扫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响动倒让我有些心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