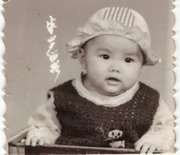这是简要的说法,全称应该怎么说,由于从来没听人说过,所以还不知道,或许祖辈们也未必清楚或愿意深究,让平静平凡平淡的日子热闹一下目的就达到了。
每到"忙毕"――也就是地里的活儿告一段落的时候,平原上就会此起彼伏的赶庙会,这边是六月二十,那边是七月初一,总之大家相互错开时间,打开尘封期年的小庙,用一台大戏或者灯影、木偶之类的小戏吸引人群、聚集目光,为神祗聚拢徒众,会就算是开始了。
我们村的庙会是七月十九,如今山上的庙已经在山下村落中央创建了分舵,方便大家朝觐,所以庙会的重头戏――东乡(凤翔在西面称为西府,所以称岐山、扶风、三元等东面的地方为东乡,秦腔在这些地方更普及,水平也高些)剧团的舞台自然也就在家门口了。
一般庙会的正日子就一天,但是庆祝(某位神仙的重要日子)要持续三天,所以大戏要唱三天四夜。事先,乡亲邻里都会得到消息,前来赶会。多日不见的人得到好的机会见面走动一番,主家自然要准备好过年一样奢华的吃食来招待,赶会是为了看戏,为了聚会,也是为了改善伙食吧。
不知道这些传统是什么人发明创办,现在看来意义更加重要,如今虽然有国庆、妇女、青年、情人等等各式各样的节日,但是真正属于农民的节日并不多,倒是祖上传下来的这些庙会是真正农民们的节日,不但村子里响动起来了,就连路上的行人也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了,人们即使不穿新衣服也是洗地干干净净的衣服,一年四季为生计四处刨挖的黑脸汉子婆姨门今日算是真正活人过日子了。
爸爸在电话中说今年是三原县剧团的戏,应该有好些年没赶过唱大戏的庙会了,我猜这大戏或许意味着今年的景程不错,这是好事。
我说给宏杰的爸妈打电话,让他们来看戏,因为我知道热闹中只有自己反倒会有另一种孤单和索然。
这个印象我小时候就有,赶庙会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很兴奋,喜欢在会场乱窜。几乎每个人回到家里都会有几辆自行车停在院子里,屋子里大人们在热闹的说话,屋外或许还有亲戚家的小孩子在玩。可是我们家却鲜有这样的场面,主要是我们家自爷爷往上几代单传,没有那么庞大的亲戚队伍,而现有的亲些的亲戚也大都相隔遥远,不能赶来。所以我总是会期待有人出现,给我个意外惊喜:在为秦腔所统治的声音世界里,会出现清脆的铃铛,我狂奔而出,期冀的人就在眼前……可是通常都没有,几个过于久远只有爷爷奶奶才能搞清楚关系的亲戚还不足以让我高兴。
如今,我们几个都长大在外,我想爸爸妈妈会更需要些许的热闹。
前几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年庙会的时候我正好在家,与我年纪相仿的那些伙伴同学都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孩子,那次的聚会在我们家院子里大瓦数的白炽灯下刨除了自家人竟然还摆起了两桌,每桌都挤的满满的,大人小孩吆三喝四好不热闹。爸爸妈妈忙前忙后却不亦乐乎,他们需要这样的热闹,或许这种孩子们的热闹对他们还有另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