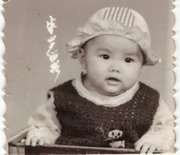1、春天来了,小朋友要去春游了。
学校组织的春游,要说远,也不远,就在城边的小山下;要说时间呢,也不长,只需要带上水和一顿午餐;小朋友呢,要说小,其实也不小了,都小学四年级了呢。
妈妈给小朋友准备好了爱喝的饮料,带上零食和两只煮鸡蛋。当然,鸡蛋是午餐的主菜加主食。
小朋友开心的去春游了,妈妈在家里迎接小宝贝归来。
到平时放学的时候,小朋友高高兴兴回来了,妈妈自然也高兴。
可是,结果小背包,妈妈发现早上准备的两个煮鸡蛋原封未动,妈妈就问原委。
小朋友说,鸡蛋上有皮,没办法吃,所以就没吃。
妈妈……
2、之前三年,大家的午餐都是围坐在会议室吃的,一边吃饭,一边八卦新闻轶闻花边闲事,偶尔也利用这个机会讲讲笑话、传达个通知。自从大院里建起食堂,这一切瞬间便成了往事。
集体聚餐吃盒饭的传统不能为继,大家似乎都不习惯。所以,同办公室或临近办公室的,或年龄等级差不多的,就相互招呼,同去吃饭,大团圆变成了小团伙。
这种形势下,其他副头儿或次头儿不在单位的时候,头儿往往会落单或者有意无意的被遗忘。
今天去吃饭,就是头儿在后面忙不迭的叫着撵上来的。
头儿气喘吁吁,说“非得我说英文你们才能听见呀,我在后面叫名字,没一个听见,非得说wait for me 你们才回头……”
是啊。大家是听见这句的时候才回头的,因为这时候声音就在身后两步的地方。
大家不禁揣测:怕是头儿已经在密集的步伐之间,把大伙儿的名字挨个叫了一遍,才……
头儿接着说,“你们走道怎么那么快!啊?”
大伙儿无语。
3、同事的小朋友上幼儿园了。
第一次总是恐怖的,小朋友肯定都不高兴。但是,没办法,总得有个开始呀,爸爸妈妈咬咬牙,留下孩子就走了。
开始的阶段为适应期,小朋友只在园里上半天课。
第一天中午,是小朋友的奶奶去接的,奶奶还未到教室,就听见哭声一片,小朋友们用鼻涕、眼泪还有竞赛般的哭声,向老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身边这些讨厌的小面团发泄不满。
奶奶心疼,紧赶两步,向老师报了姓名要孩子。
第一天嘛,老师也不知道哪个代号是哪个小朋友的,喊了半天,下面的小朋友大多在嚎,没人搭理她。她只好出来问孩子穿的啥衣服,奶奶讲了,老师很快报出一个来,奶奶一看不是,只好自己进去把小朋友抱出来。
奶奶问,老师叫名字咋不答应呢?
小朋友说,小朋友都哭,我只好自己玩呢,老师也没叫我呀。
奶奶说,那老师叫啥?
老师在上面喊楚湘呀?
那你叫啥呢?
我叫湘湘。
……
4、小朋友上幼儿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大家都已经适应多了,即使是全天也没关系。
昨天是湘湘第一天全天“上班”,“下班”回来,晚饭吃得特别多:自己吃完一碗饭,还要吃一碗,吃晚饭还要喝汤……
妈妈很奇怪,问没吃午饭呀?
湘湘说,吃午饭了,我没吃饭。
妈妈说,为什么?
湘湘说,小朋友们吃饭的时候,我在东张西望。
妈妈,……!!!
这是湘湘上幼儿园之后,嘴里蹦出的第一个成语,不过妈妈揣测,这个词大概是这么学来的:
别的小朋友都在认真吃饭,只有湘湘不好好吃饭,摇头晃脑,于是老师说,不要东张西望……
湘湘就记住且明白,她当时没做吃饭这件事情,而是在做东张西望这件事。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2008年3月8日星期六
生机勃勃
我相信,她们都已经习惯这里,并且打算在这里落地生根。
富贵竹最先焕发精神,逐渐长出根须,并且换上了层次清晰得嫩绿装束,客厅的一束已经长得很高达。
青苹果得嫩叶是忽然发现得,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一支卷筒状得嫩叶笔直得站在一群开阔得叶子中间,然后花了几天时间,逐渐打开,如今已经大模大样的跟她那些前辈一样闪烁着风姿。
虎皮兰的花盆里忽然冒出蒜瓣大笑的嫩芽儿实在是一场惊喜,这个小家伙现在长得很快,细细数一下,已经有四个小尖尖了,将来花盆里的第四束虎皮兰应该至少有四支。
小口杯里五片叶子的绿萝马上就要分蘖,从心生的第五片叶子的叶柄上长出第六片了。
橡皮树一直很沉默,曾经陆续掉过几片靠近根部的叶子,很长时间,她都保持着固有的矜持,看不出什么变化。不过,今晚终于有新发现,一株枝尖上嫩紫的芽儿终于有些变化,近乎要打开,第一片新叶子长出来应该指日可待。
2008年2月3日星期日
响动
习惯标准语言的人似乎不怎么用这个词,为找到这个词我竟然费了好半天劲儿,证明我也不知不觉皈依了标准派,这个历程近乎十年。但是,似乎我六根未净,并未真正皈依,对家乡的表达方式略显生疏之后,却并未对标准语言有所精进,结果现在不论是论起“道”来还是说起“书”来,连自己都感觉索然。
既然找到了响动这个词,还是返回来继续说响动。
老家的房子一般都有阁楼,所谓阁楼并不是西洋电影里那种可以居住的小半层屋子,只是为了让屋子的空间更紧凑,不至于躺在炕上,坐在椅子上就看见屋顶上的梁椽,在屋檐的高度顺着椠架上死条木梁,篷起一个平整的天花板而已。这个天花板因人而异,有实力的人家,用的平整的木板,整齐密实,就像现在城里人铺地板那样,弄一个天花板,这样的天花板上放的空间可以成为真正的阁楼,其高度虽不可以居住,但其牢靠程度却足以把成石的粮食存在上面。没实力的人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一而足,当然最简单的是什么都不做,除此而外,一般会用芦席加细竹棍儿篷上,下面再糊上报纸、小孩的正反面写过的作业本之类的。
详尽的解释老家的阁楼,通常犯这样的毛病恐怕是潜意识作祟,那个不只是本我还是自我还是什么我的家伙在谴责我不要忘记,而我却常常不会想这些陈芝麻,所以忘本的内疚或者健忘的惶惑让我染上了絮叨的毛病,今天倒不是这样的情形,显然阁楼的事情是我主动想起来、说起来的,解说它的原理,是因为最初对于响动这个词的生动理解是从它而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随着爷爷奶奶睡,那一段时间“响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爷爷奶奶的瞌睡已经不像我那么多了,所以,对于阁楼上老鼠的响动,他们总是很敏感。有一段,老鼠特别猖獗的时候,奶奶会在枕边准备一支细长的竹棍,用它来对付半夜出动的老鼠。当老鼠在黑暗中快速跑动时,奶奶的芦席顶棚便会火车驶过一样,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这个时候,奶奶就会挥动竹棍,胡乱敲打几下,制造些声响,让那轰隆声止歇一会儿。
我猜想那些半夜来我家顶棚上的老鼠,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要是放在解放前,我们家的木头阁楼上或许会有成囤的粮食,那个时候要粮的角色多,跑开穿各色制服的,还有土匪什么的,粮食放在阁楼上或许还有希望逃过一劫,那年头像我们家这样需要亲自挑着筐拾粪、自己下地干活、吃花面馍的小地主,估计是真正的“地主家也没余粮”。但有的话,应该肯定在阁楼上。
所以,从旧时代,估计老鼠们就口口相传,形成了阁楼上有粮食的共识,及时是时代变了,我家的木板阁楼变成芦席顶棚,木板阁楼时代那些老鼠的后代们还都执着于他们的传统,用他们轰隆隆火车般的跑动,搅扰奶奶的水面,要奶奶听见他们的动静,就要制造代表主人存在的响动。
那个时候,我形象的记住了奶奶说的响动这个词,其实应该是动响,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
关于响动的第二层含义,与响器这个词有关,响器无处不在,但在寺庙、锣鼓队、乃至吹鼓手、剧团里到处都是。村里唱大戏,有经验的大人们,总是在舞台那边传来吹打声的时候,才背起手,慢悠悠的出发,性子急的人就会说,台子上已经响动开了,得赶紧些。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终年宁静的村子上空忽然飘动的响动,常常会让我们激动地不知所措,既想在戏台周围乱窜,不错过任何热闹和大家的目光,又向不错过院子来之不易的响动,那响动远远的传来,有些空空旷旷,却充盈于每个人心里,告知大家我们处在不同以往、易于平日的时间和事件中。
我始终没有学会向作家描写夕阳像闯祸的篮球跌进窗花那样,描绘让自己激动乃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在某些时候,摆脱不了那种情境:既是热闹人群中的一员,又能抽身出来看到包括自己的热闹人群,就像自己想看到自己开着的车子在路上怎样行使那样。
从小年夜开始的爆竹声今晚依旧,城市的夜空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变得活泛了一些,我知道那些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散播到空气中除了火药的香味,还有放鞭炮的人难得的一个人面向位置数目的大众无拘无束的表演和宣告。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除夕夜仔细回味连绵不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我知道那响动中有众神在蹒跚中享用烟火,还有就是远远近近、各不相同的人在夜空中相互传达着相似的信息,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满满的,因为我知道我的鞭炮声别人也已经听到了。于是,这响动又会我的激动乃至不知所措,在除夕的夜晚不想睡觉,有无所事事,于是,我就回想:鞭炮大概是放给远方乃至过去的人听的,我要是能在远处听自己放的鞭炮就好了,就像除夕之夜,偷偷出来看窗花彩联的窗前漏出的喜庆那样。明天要回家团聚了,今晚在家洒扫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响动倒让我有些心慌。
既然找到了响动这个词,还是返回来继续说响动。
老家的房子一般都有阁楼,所谓阁楼并不是西洋电影里那种可以居住的小半层屋子,只是为了让屋子的空间更紧凑,不至于躺在炕上,坐在椅子上就看见屋顶上的梁椽,在屋檐的高度顺着椠架上死条木梁,篷起一个平整的天花板而已。这个天花板因人而异,有实力的人家,用的平整的木板,整齐密实,就像现在城里人铺地板那样,弄一个天花板,这样的天花板上放的空间可以成为真正的阁楼,其高度虽不可以居住,但其牢靠程度却足以把成石的粮食存在上面。没实力的人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一而足,当然最简单的是什么都不做,除此而外,一般会用芦席加细竹棍儿篷上,下面再糊上报纸、小孩的正反面写过的作业本之类的。
详尽的解释老家的阁楼,通常犯这样的毛病恐怕是潜意识作祟,那个不只是本我还是自我还是什么我的家伙在谴责我不要忘记,而我却常常不会想这些陈芝麻,所以忘本的内疚或者健忘的惶惑让我染上了絮叨的毛病,今天倒不是这样的情形,显然阁楼的事情是我主动想起来、说起来的,解说它的原理,是因为最初对于响动这个词的生动理解是从它而来的。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随着爷爷奶奶睡,那一段时间“响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爷爷奶奶的瞌睡已经不像我那么多了,所以,对于阁楼上老鼠的响动,他们总是很敏感。有一段,老鼠特别猖獗的时候,奶奶会在枕边准备一支细长的竹棍,用它来对付半夜出动的老鼠。当老鼠在黑暗中快速跑动时,奶奶的芦席顶棚便会火车驶过一样,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这个时候,奶奶就会挥动竹棍,胡乱敲打几下,制造些声响,让那轰隆声止歇一会儿。
我猜想那些半夜来我家顶棚上的老鼠,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要是放在解放前,我们家的木头阁楼上或许会有成囤的粮食,那个时候要粮的角色多,跑开穿各色制服的,还有土匪什么的,粮食放在阁楼上或许还有希望逃过一劫,那年头像我们家这样需要亲自挑着筐拾粪、自己下地干活、吃花面馍的小地主,估计是真正的“地主家也没余粮”。但有的话,应该肯定在阁楼上。
所以,从旧时代,估计老鼠们就口口相传,形成了阁楼上有粮食的共识,及时是时代变了,我家的木板阁楼变成芦席顶棚,木板阁楼时代那些老鼠的后代们还都执着于他们的传统,用他们轰隆隆火车般的跑动,搅扰奶奶的水面,要奶奶听见他们的动静,就要制造代表主人存在的响动。
那个时候,我形象的记住了奶奶说的响动这个词,其实应该是动响,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
关于响动的第二层含义,与响器这个词有关,响器无处不在,但在寺庙、锣鼓队、乃至吹鼓手、剧团里到处都是。村里唱大戏,有经验的大人们,总是在舞台那边传来吹打声的时候,才背起手,慢悠悠的出发,性子急的人就会说,台子上已经响动开了,得赶紧些。
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终年宁静的村子上空忽然飘动的响动,常常会让我们激动地不知所措,既想在戏台周围乱窜,不错过任何热闹和大家的目光,又向不错过院子来之不易的响动,那响动远远的传来,有些空空旷旷,却充盈于每个人心里,告知大家我们处在不同以往、易于平日的时间和事件中。
我始终没有学会向作家描写夕阳像闯祸的篮球跌进窗花那样,描绘让自己激动乃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但即使是现在,我依然在某些时候,摆脱不了那种情境:既是热闹人群中的一员,又能抽身出来看到包括自己的热闹人群,就像自己想看到自己开着的车子在路上怎样行使那样。
从小年夜开始的爆竹声今晚依旧,城市的夜空在一年到头的时候,变得活泛了一些,我知道那些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散播到空气中除了火药的香味,还有放鞭炮的人难得的一个人面向位置数目的大众无拘无束的表演和宣告。
小时候,我就喜欢在除夕夜仔细回味连绵不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我知道那响动中有众神在蹒跚中享用烟火,还有就是远远近近、各不相同的人在夜空中相互传达着相似的信息,这个时候,心里就会觉得满满的,因为我知道我的鞭炮声别人也已经听到了。于是,这响动又会我的激动乃至不知所措,在除夕的夜晚不想睡觉,有无所事事,于是,我就回想:鞭炮大概是放给远方乃至过去的人听的,我要是能在远处听自己放的鞭炮就好了,就像除夕之夜,偷偷出来看窗花彩联的窗前漏出的喜庆那样。明天要回家团聚了,今晚在家洒扫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响动倒让我有些心慌。
2008年2月2日星期六
史记·列子2007
断章取义余华小说里的话:“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抒情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士兵突击》总结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2007年热映的几部电影让人们得出如下结论:《色戒》指出女人不可靠,《投名状》揭示兄弟靠不住,《集结号》以其杂糅的风格、片段的叙事和空洞的内容表明“连他妈的组织都靠不住”。
胡紫薇同学在C视奥运道场开播发布会上的宣言,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位法国外交家的名言,也以“典型的法国评判标准”宣告我国“竟然”成不了大国!
刘震云说,偷东西被抓住或者没被抓住的都不是贼,也就是说偷东西不是贼,以名门正派、正剧面孔、高谈阔论窃取、置换精神的才是贼,真正的贼。
就在这一年,吓大的一位历史教授在C视的教授快板书(评书?)大行其道,吃饭大学的全能女人发挥传媒优势、动用古典文学的根基,在传统仁义道德的废墟上重新发现有着爽滑口感和糖衣蟹黄的河蟹精神,以空虚生发空洞、用连珠妙语铸就空口道理论体系,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跨媒介、跨学科的生动实践。
佚名同志曰“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书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留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留言……”
史太公评曰:佚名先生虽言语有失偏激,但却凝练清晰,因故得与快板书教授、全能女人、烈女胡氏等等同入列子。又怒曰,看前面洪洞洞(注:2007年,在当年苏三的家乡,警方成功从黑砖窑解救出数名”包身工”,据传,这些包身工因未能及时冲破历史时空,先后被滞留在苏三时代以及夏老的包身工时代。),贼人哪,贼!哇~啊呀呀。
《士兵突击》总结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2007年热映的几部电影让人们得出如下结论:《色戒》指出女人不可靠,《投名状》揭示兄弟靠不住,《集结号》以其杂糅的风格、片段的叙事和空洞的内容表明“连他妈的组织都靠不住”。
胡紫薇同学在C视奥运道场开播发布会上的宣言,让全国人民知道了一位法国外交家的名言,也以“典型的法国评判标准”宣告我国“竟然”成不了大国!
刘震云说,偷东西被抓住或者没被抓住的都不是贼,也就是说偷东西不是贼,以名门正派、正剧面孔、高谈阔论窃取、置换精神的才是贼,真正的贼。
就在这一年,吓大的一位历史教授在C视的教授快板书(评书?)大行其道,吃饭大学的全能女人发挥传媒优势、动用古典文学的根基,在传统仁义道德的废墟上重新发现有着爽滑口感和糖衣蟹黄的河蟹精神,以空虚生发空洞、用连珠妙语铸就空口道理论体系,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跨媒介、跨学科的生动实践。
佚名同志曰“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书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留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留言……”
史太公评曰:佚名先生虽言语有失偏激,但却凝练清晰,因故得与快板书教授、全能女人、烈女胡氏等等同入列子。又怒曰,看前面洪洞洞(注:2007年,在当年苏三的家乡,警方成功从黑砖窑解救出数名”包身工”,据传,这些包身工因未能及时冲破历史时空,先后被滞留在苏三时代以及夏老的包身工时代。),贼人哪,贼!哇~啊呀呀。
2008年2月1日星期五
长江7号
刘震云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论述听上去很辩证,大致的意思是悲剧的核是喜剧,而喜剧在往上才是真正的悲剧。就像人的生死两头很显然是悲剧,哭着来到世上,然后在别人的哭声中去往“一劳永逸的长眠”(这个是余华的话),而中间部分则是以各种各样的喜剧进行的。
《长江7号》似乎在印证这位作家的论断。
如果作为儿童片,《长江7号》绝对是纯粹意义上好看好玩的儿童片,小孩子的幼稚与狂妄想法、以及小孩子之间那些“残忍的好奇心”促成的种种事件,被夸张而准确的展现出来,加上那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独创的、天真可爱外加周星驰式调皮外星机器狗“7仔”,绝对能让小孩子度过一段开心时光,然后在内心里种下向善的种子。至于大人,如果不被所谓专业眼光毒害的太深,或者还不至于早衰式的死气沉沉肌肉僵硬,估计也会忍不住会心一笑,在瞬间远离眼下这在如浮沉般翻滚的新闻中变得更加寒冷冰冻而且有些沮丧的冬天。
但是,周星驰这次演的是个民工。用片中儿子的话说,爸爸的职业是:做民工。这位父亲邋遢黑瘦,要在他做建造的水泥大楼顶上吃盒饭,蹲在商店橱窗外看电视,想尽办法来疼爱并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己无法拥有尊严或者得到尊重,那就要让孩子与自己不同。
尽管他对用“柔软的方式来面对坚硬的现实”这种方法早就稔熟于心,故事也试图用外形机器狗狗的神力来遮盖或者置换他注定的命运,但情感的转移以及他的死而复生却更加让人感觉世事炎凉,蜻蜓点水般触摸到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
我们在看大陆电影(现在似乎港片以及合拍片都统称国产片了)的时候,或者看港片偶尔联想对照到大陆片的时候,会轻易就顿悟:哦,我们所谓影星在电影里塑造的是自己,而人家所谓的艺人往往能成为角色。自从有一天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吃惊竟然有初中生批判大陆电影以及所谓的电视电影:“我坚持我下看,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还能假到什么地步”。
很多因素决定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标准,就像单位里你会是局长、老张、小李,而在社会上你变成干部、城里人、乡下人,城里人又分成白领啊、干部啊、工人啊什么的,乡下人里当然也有干部,但对乡下人的准确称为应该是农民和民工,前者说明他的户口所在地、真实职业以及所谓文明程度,后者旨在揭示其在高度文明的现代大城市里的地位,首先要表明是个外来者不是主人但也绝对不是客人,然后是低标准生活的主体,不懂规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应该必需承担挖地沟、捡破烂、倒垃圾、修管道等等所有苦力范畴内的活儿,而且应该感恩戴德。
然后,所有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等都自然而然淹没在这些身份概念之中,如果直白的说,就是身上戳有肉牛、种牛或者耕牛之列标签的畜生?!!!
既然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既然我们是坚决的唯物主义者,既然我们信奉物质决定意识,既然物质也就是客观存在(记不清楚了),那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意识与物质的相互纠缠,有意为之的张扬和深藏不露的隐匿之中,生活的正剧无可逆转的就变成了喜剧。
《长江7号》似乎在印证这位作家的论断。
如果作为儿童片,《长江7号》绝对是纯粹意义上好看好玩的儿童片,小孩子的幼稚与狂妄想法、以及小孩子之间那些“残忍的好奇心”促成的种种事件,被夸张而准确的展现出来,加上那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独创的、天真可爱外加周星驰式调皮外星机器狗“7仔”,绝对能让小孩子度过一段开心时光,然后在内心里种下向善的种子。至于大人,如果不被所谓专业眼光毒害的太深,或者还不至于早衰式的死气沉沉肌肉僵硬,估计也会忍不住会心一笑,在瞬间远离眼下这在如浮沉般翻滚的新闻中变得更加寒冷冰冻而且有些沮丧的冬天。
但是,周星驰这次演的是个民工。用片中儿子的话说,爸爸的职业是:做民工。这位父亲邋遢黑瘦,要在他做建造的水泥大楼顶上吃盒饭,蹲在商店橱窗外看电视,想尽办法来疼爱并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己无法拥有尊严或者得到尊重,那就要让孩子与自己不同。
尽管他对用“柔软的方式来面对坚硬的现实”这种方法早就稔熟于心,故事也试图用外形机器狗狗的神力来遮盖或者置换他注定的命运,但情感的转移以及他的死而复生却更加让人感觉世事炎凉,蜻蜓点水般触摸到我们熟视无睹的生活。
我们在看大陆电影(现在似乎港片以及合拍片都统称国产片了)的时候,或者看港片偶尔联想对照到大陆片的时候,会轻易就顿悟:哦,我们所谓影星在电影里塑造的是自己,而人家所谓的艺人往往能成为角色。自从有一天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吃惊竟然有初中生批判大陆电影以及所谓的电视电影:“我坚持我下看,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还能假到什么地步”。
很多因素决定了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标准,就像单位里你会是局长、老张、小李,而在社会上你变成干部、城里人、乡下人,城里人又分成白领啊、干部啊、工人啊什么的,乡下人里当然也有干部,但对乡下人的准确称为应该是农民和民工,前者说明他的户口所在地、真实职业以及所谓文明程度,后者旨在揭示其在高度文明的现代大城市里的地位,首先要表明是个外来者不是主人但也绝对不是客人,然后是低标准生活的主体,不懂规矩,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应该必需承担挖地沟、捡破烂、倒垃圾、修管道等等所有苦力范畴内的活儿,而且应该感恩戴德。
然后,所有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等都自然而然淹没在这些身份概念之中,如果直白的说,就是身上戳有肉牛、种牛或者耕牛之列标签的畜生?!!!
既然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广泛存在,既然我们是坚决的唯物主义者,既然我们信奉物质决定意识,既然物质也就是客观存在(记不清楚了),那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意识与物质的相互纠缠,有意为之的张扬和深藏不露的隐匿之中,生活的正剧无可逆转的就变成了喜剧。
2008年1月31日星期四
喜剧时代
胡紫薇同学演的那出独角戏,尽管借助了cctv和奥运的名头,试图以这样的喜剧方式让全国人民辞旧迎新,但她忘了这是个啥时代,这样立贞洁牌坊、发表关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宏论的方式,不会被谁记住几天的,何况2008年的1月还有更重大的事件呢。
不知道这个事件算不算是喜剧,但是对于前一段时间来京赶考的老孙两口子来说,应该算是个喜剧——顺利在大雪冰冻对我国的道路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之前赶回贵州,尽管回去之后付出了双双感冒的代价,还要忍受2块钱1斤白菜的代价,但总算是没在某个铁路小站连续数天欣赏雪景。
但是,大多数人却要接受严酷的事实,尤其是已经聚集在列车车厢、车站还有公路上的人们,春节团聚这样壮观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似乎只有这样才绝无仅有的显示出了一次诗意,而往年拥挤一下就怨声载道、怒气冲冲的表现,要是在这次的风雪严寒中再回顾,就显得幼稚不堪了。
春节不会等着谁,所以,我们的形势总还是一片大好的,就像那些成天关注武器、军力还有打仗的人那样,我们自信我们的国明经济是强大的,这不,有人就拿出了我们正在建造航母的又一铁证么:
 我们的语言再次现实出其幽默性,就像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一样让人咂舌。
我们的语言再次现实出其幽默性,就像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一样让人咂舌。
生活在喜剧年代,需要有喜剧精神,还要有欣赏喜剧的精神。
不知道这个事件算不算是喜剧,但是对于前一段时间来京赶考的老孙两口子来说,应该算是个喜剧——顺利在大雪冰冻对我国的道路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之前赶回贵州,尽管回去之后付出了双双感冒的代价,还要忍受2块钱1斤白菜的代价,但总算是没在某个铁路小站连续数天欣赏雪景。
但是,大多数人却要接受严酷的事实,尤其是已经聚集在列车车厢、车站还有公路上的人们,春节团聚这样壮观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似乎只有这样才绝无仅有的显示出了一次诗意,而往年拥挤一下就怨声载道、怒气冲冲的表现,要是在这次的风雪严寒中再回顾,就显得幼稚不堪了。
春节不会等着谁,所以,我们的形势总还是一片大好的,就像那些成天关注武器、军力还有打仗的人那样,我们自信我们的国明经济是强大的,这不,有人就拿出了我们正在建造航母的又一铁证么:
 我们的语言再次现实出其幽默性,就像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一样让人咂舌。
我们的语言再次现实出其幽默性,就像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一样让人咂舌。生活在喜剧年代,需要有喜剧精神,还要有欣赏喜剧的精神。
订阅:
评论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