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故事的印象纠结在一起,在脑袋里打起了浆糊。我猜大概不是因为故事不好,不能给人留下鲜明些的隐形,只是这些故事以及里面的人有些像,不那么精确的概括的话,是他们的身份比较像:来城里的乡下人,这些人都希望能够在城里有一个位置,然后像城里人一样活得体体面面。
作家自然而然的把这些人放在城市这个巨大的鏊子上来翻转,带出来的意识也是明显的,作家要总结、提炼生活,心里怎么也得有写条条框框,人群要分出阶层才好分析表现他们源自出身的性格和价值观念,何况生活当中,阶层、利益群体的观念本来就在日渐深入人心,大概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的艺术的特质和他留给人的特有印象:从来都是缺少独立的情感、心里逻辑,而无论什么类型风格的创作,都会多多少少带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道德评判方面的理论模式,人往往小之又小,不知道跟现实中个体的渺小相比如何,总是人拖泥带水,从来都出落不干净。
很多时候,人只不过是个活动的物件,用物件做代号区分。以前只要看到农村戏,我们就总会看到柱子、石头、墩子之类物件被呼来唤去,还有什么嘎子、楞子、二蛋、狗剩等等怪模怪样的物什,村里的干部除了村长就是老支书,没有一个不七老八十又叼着烟袋的,这是以前当然也延续到现在的艺术家创造的世界(他们并不知道当代的初级行政机构里面,已经去掉了“村长”这样的头衔),叫啥都一样,名字在一定阶层和范围内可以通用,而人不用分彼此;米粒儿,这倒是一个新鲜的名字,先看到的是一个城市小姑娘的名字,看上去有几分可爱疼爱的意思,后来,这个时髦化的物件型名字还是回到了乡下,《米粒儿的理想》中“我”一厢情愿数十年的梦中情人、结婚对象就叫这个名字。时髦是时髦了,还是逃不了物件的命运。
米粒儿是“我”青梅竹马的人儿,“我”虽然始终没敢对米粒儿表白,但是却知道米粒儿的理想,要挣很多钱,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当然,这个理想是米粒儿考大学之前发奋学习时候的想法。米粒儿没能考上大学,对“我”是一件好事,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挣够钱娶她。“我”的故事的缘起大概就是这样,对乡下童年的记忆很短,当然也最有意思,光“我”老嘘这个名字的来由,就能说明“我”有多么金贵。但是,“我”刻骨铭心难忘的还是在城里的经历,尽管“我”像许三观、李大头、孙国民那样流浪生活,想尽办法、历尽磨难、投机取巧、偷鸡摸狗的挣钱,还是不能赶上先做保姆,后来在发廊被三哥发现称为大公司秘书的米粒儿的成功,“我”的钱始终不够,也永远赶不上米粒儿见识过、知道的世界。米粒儿是女人,有捷径可走,而我们都知道彼此真实的样子却没必要坦白了。
《孝子》里面的女孩记不清叫啥了,重点大学毕业,通过婚姻在省城站住了脚,故事却把她拉回了她降生的小巷,这个小地方走出去的女人鄙视这里,但却永远和这里扯不清关系;《我爱你深圳》,出来深圳找老婆回家给父母包孙子的水库跟老婆做了同事,在宝安区最高的楼里当保安,而媳妇则干着清洁组长的工作。经过对大厦和城市的眩晕感之后,水库开始在城市里有了隐秘的自己的生活,但是老婆这个经见过大城市的人忽然提出一个方案:两人分别找一个深圳人多好。
想必不是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们的欲望太多,只是,现实制造了不同的身份和别样的生活,四处喷射的诱惑像烟花一样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何况还是有潜伏水面之下的浮桥可以抵达彼按……
(小说中)生活似乎无处不充满愁苦,估计作家还是在忧国忧民的创作,只是人还是传统的模样,忘不了天底下总有尊卑、高下这样的东西,记不起自己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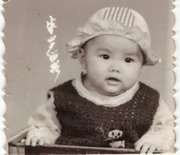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